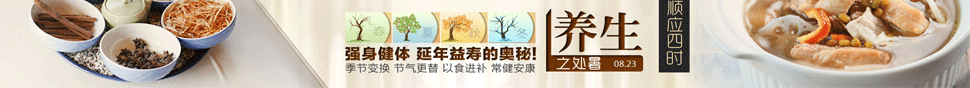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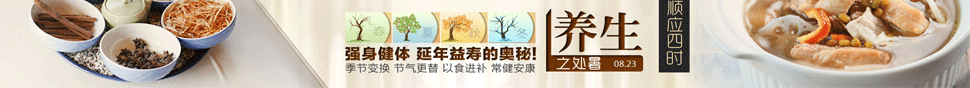
我曾无数次从秋季的夜雨里惊醒过来。惊醒是短暂的。窗外不绝的雨声,仅仅只能捕捉到几秒罢了。模糊地听见后,便总是像得到了慰藉一般安心下来,再度沉沉睡去。
不过,在分不清楚是梦还是现实的那一瞬的雨声中,我总隐隐约约地看见一个男子。
你试过八月末尾时,走在北海道初秋那连绵不断的雨中吗?那是怎样的一种雨:空气里浮动着冷杉和落叶松的清香,远处的天空半阴,黑和白的云在静谧中将对方撕裂。细密的斜针一根根插入湖面。
我爱用“灰色”形容雨。北海道的雨,许是如雏鸭绒毛般湿而柔软的浅灰吧。
两场雨的间隙中、一个难得的晴天,我在札幌偶遇了卡拉瓦乔的画展。尽管刚下了电车便发现市内各处都贴满了展览海报,但那时候,除了“是个名画家”这种泛泛的概念,我还搞不太清卡拉瓦乔具体是谁,也尚且不能通过日文假名拼出他的名字。
当时的票根,现在仍完好保存着
走路到北海道立近代美术馆很快。除海报上那幅卡拉瓦乔扮作酒神的著名自画像,馆内还展出了他众多描绘拷打、斩首及死亡场面的宗教题材油画。印象中看到《犹迪杀死荷罗浮尼》、《大卫手提戈利亚的头》,都颇为触动。
然而众多的处刑画中,只有一张令我全身心地震撼。
那是一幅竖立的男子全身像,画中人物足有一人高,他被悬挂在血色的墙壁上,仿佛正在做火刑前示众的展览。绝美的古希腊式的男性胴体仅由一道白绸布遮过腰间,立在日与夜的狭缝之间,两手反绑,微微垂下头颅。两个埋首于阴暗中的人正将麻绳扯过那双强健细腻的小腿,三人构成了诡异的三角形;一支箭刺穿年轻男人的肋间,在那里闪着幽幽寒光。
伤口处看不到血,然而他脚下铺开的猩红的衣物,竟宛如在寂静中正流淌着一样,使我产生了空气里都弥漫起腥味的错觉。
画面上的光与影是那么激烈而暴戾,像美杜莎的蛇发般溢着魔力。我为之呼吸凝滞,久久伫立,无法移开视线。我后退几步以观赏全景,又忍不住再走上前近距离地细看,视线与男子那丘陵般起伏着的、略泛潮红的两膝平齐;接着又被那浓郁热烈的笔触所震慑,不得不倒吸口凉气,再度跌跌撞撞地后退。就这样,来回徘徊了许久,呼吸才渐渐平稳了下来。
回去后的那天晚上我做了梦。很奇怪——一般来讲,旅行中我因过度疲劳几乎从不做梦。梦的内容已忘记,只知道那是惨绝人寰又光怪陆离的噩梦,梦里的天空是灰色,草地是灰色,有人在奔跑,有人在死去,一切都是潮湿的灰色。我的头上没有屋顶,却只能听到而看不到雨,雨声滂沱,淹没一切。第二天的早晨,我面对着挂满了水滴的窗和津湿的街道醒来。
之后的日记中,我写下一句“我找不到那幅画。”之所以找不到,是因为馆内不许拍摄,而我明明已记下了画作的标题,去找寻时却弄错成同一场展览看到的施洗者圣约翰像了。加之那在卡拉瓦乔的作品中,原本就属于相当鲜为人知的一件。
说起来,画中猛地击中我灵魂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呢?以前的思考中,似乎觉得自己是在顷刻间被其中喷涌而出的情欲洗过,深受感动;但我似乎混淆了“性爱”和“流血”的概念。在那时候,我认为二者已然一体,再没有彼此的分别。后来阅读到他人所写观赏画作时感受到“性欲”的体验,我竟一点都不能产生共鸣。所以,也许是为画作本身阴暗颓靡的气质和其显示出的不祥预兆而恐惧?又或者是被那男子纯粹而圣洁的美打动?还有可能,是从他那低垂的眼帘里读出了某种对尘世众生的悲悯,聆听到了超自然的宿命力量的感召?
很难下结论。当时的我,抑或现在的我,都说不清楚。
高中美术课很快介绍到了卡拉瓦乔。我去请教老师,虽仍未确认这张作品的身份,但得到了关键信息——宗教画中身中数支箭矢的男人,是一位名为塞巴斯蒂安的圣徒。
圣塞巴斯蒂安是公元三世纪人,他在米兰长大期间皈依了基督教。当时的罗马人信奉希腊诸神,新兴的基督教被视为异端,戴克里先皇帝对他们实施严酷的镇压政策。参军来到罗马后,塞巴斯蒂安得到戴克里先的赏识,被提拔为近卫队长。传说他是一名信仰虔诚、热衷布道的信徒,不仅利用职权安慰狱中的基督徒,还极力劝告同仁改宗。很快,他的“背叛”行为遭人告发,戴克里先判处他被乱箭射死。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他身中万箭的形象得到后来画家们广泛描绘、某种程度上也成了他的标志,圣塞巴斯蒂安却并不是因此而死。圣徒艾琳将重伤的他救活后,他又来到戴克里先面前斥责了他的信仰。这一次他在皇帝令下被乱棍打死,尸体抛进了罗马的下水道。民间也流行另一种说法,即戴克里先是对塞巴斯蒂安爱而不得才将之杀死,但我以为不大可信。
早期关于圣塞巴斯蒂安的艺术作品极少,并且其中呈现出的他的形象,与我们现在所熟知的俊美年轻人完全不同。在中世纪,他常被表现为一个头顶光圈、手持桂叶的白胡子大叔。
意大利拉凡纳拜占庭教堂的一幅马赛克(-年)。左起第四位,袍子上写着字母“O”的即为圣塞巴斯蒂安。
年,黑死病开始在欧洲肆虐,几乎半数的人口都死于这场浩大的灾难。于是,恐慌的人们开始向圣塞巴斯蒂安祈祷——有一种说法是,人们认为瘟疫病人所受之苦和圣塞巴斯蒂安的受难具有相似性;另外,《圣经》中箭的意象常被用来象征神施加于世的疫病和惩罚,而圣塞巴斯蒂安却在被无数箭头射中后,也奇迹般地存活。彼时,这位被赋予了“瘟疫保护神”的新角色的殉教者,便开始频繁地以受刑中箭的形象在画中出现。
箭矢,俨然成为了圣塞巴斯蒂安的符号、圣塞巴斯蒂安的宿命。他不死于箭:箭是他的死亡预告。就像那幅卡拉瓦乔的画作一样——垂直的画框无异于檀木棺材那镶金的边沿。在万籁俱寂的午夜,塞巴斯蒂安被悬于盖亚1怀抱的上方,早已了然自己的命运,正静默地等待着被她拥入。
也有庄严肃穆、充满着受难意味的圣塞巴斯蒂安像。
《圣塞巴斯蒂安》()安德烈亚·曼特尼亚
圣徒被绑缚于损毁的科林斯式直柱之前,略显老态的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他那洁白紧实的肌肉,似乎与身后的大理石同样坚硬;但同时他又像无助的猎物,身上插满多于必要致死数目的箭,就仿佛那些箭是异教徒们为了使得这场殉教更加戏剧化,而刻意摆放于他血肉之间的祭品。
这幅画像里是读不到情色感的。你很难在这样的一个塞巴斯蒂安身上窥到一些性虐的愉悦;连他腰间的绸布都遮蔽了更大的面积,显得臃肿多余。
也有古典英雄式的圣塞巴斯蒂安。
《圣塞巴斯蒂安》()提香·瓦切列奥
作为提香晚年的作品,这个时期的圣塞巴斯蒂安已经脱离了先前被插成刺猬的呆板造型,体态也更为年轻。画中的他无疑是美的,或者说被加以了美的再造。阴风呼啸的混沌天空之下,那副优美的身姿遗世独立,如纪念碑一般岿然不动。背景与前景杂在了一起,几抹血污肆意吻过青年的侧腹和大腿,给这具勃发着卓越生命力的矫健肉体平添一份绝望感,令人战栗。
这样癫狂、壮丽而瑰异的圣塞巴斯蒂安像是极少的。与其说他在受刑,不如说他在战斗——在战场刀剑相撞而碰出的火花中,被流箭射下马来——那倒才是更适合近卫队长的死法呢。
当然还有情色的塞巴斯蒂安。情色的塞巴斯蒂安,下一部分中再予以介绍。不过,至于圣塞巴斯蒂安是怎么从拜占庭式的强壮中年男人,摇身一变成为了巴洛克式的美少年,恐怕这并非只是几位同性恋画家个人的兴趣所能解释的。从14世纪起,人们对基督教艺术的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在私人崇拜的作用下,艺术家们开始对“共情”更感兴趣,并把画作当作感受耶稣和其他圣人苦难的方式。
如此一来,若讲得极端一点:那些热衷于圣塞巴斯蒂安题材的画家们,以及古往今来沉湎于圣塞巴斯蒂安之美的男男女女,是否都多少有些许受虐的倾向呢?
这个英俊青年被赤裸着身体捆绑在那黑树干上,让他的双手高高地交叉着,并将捆绑双手的绳索系在树上。此外看不见绳结。遮掩青年裸体的,只有一块松弛地缠在腰身周围的白粗布。
连我也能够判断出那是一帧殉教图。但是,文艺复兴时期最后的唯美的折衷派画家所描绘的这副圣塞巴斯蒂安殉教图,毋宁说洋溢着异教的氛围。因为在这堪与安提诺乌斯媲美的肉体上,没有其他圣者们身上通常所看到的那种布教的艰辛与老朽的痕迹,唯有青春、唯有闪光、唯有美、唯有逸乐。
这白皙的无与伦比的裸体被置在薄暮的背景前,熠熠生辉。他身为近卫军而习惯于拉弓挥剑的健壮的臂膀,是在那样合理的角度被抬了起来,他被捆绑的手腕恰好交叉在他头发的正上方。他的脸,微向上仰。望着苍穹荣光的眼睛,深沉而安详地睁大着。无论是挺起的胸膛、紧缩的腹部,还是微微扭曲身子的腰部周围,都飘逸出一种不是痛苦,而是音乐般的倦怠的逸乐的震颤声。要不是箭头深深射进他的左腋窝和右侧腹的话,他这副模样就像罗马的运动健将,凭依在薄暮的庭院树旁休息,以恢复疲劳的样子。
箭头深深地扎进他的紧缩而结实的、四溢香气的、青春的肉体里,欲图以无上的痛苦和欢悦的火焰,从内部燃烧他的肉体。但画家没有画流血,也没有像其他塞巴斯蒂安图那样画无数的箭头,只画了两支箭落在他那大理石般的肌肤上,宛如平静而端丽的枝影投落在石阶上一样。
上面的文字引自三岛由纪夫《假面的告白》。这部自传文学中,他以浓重的笔墨描写了圣塞巴斯蒂安之美,记录了一幅殉教图对自己的性启蒙意义。意外的感冒留家,让他面对着画册上一幅圭多·雷尼所绘的《圣塞巴斯蒂安》实现了“人生第一次ejaculatio”2。
实际上,雷尼曾许多次重复这同一主题,前前后后大约画过9件不同的《圣塞巴斯蒂安》。根据文中的描述,推测三岛所看到的《圣塞巴斯蒂安》大约是下面这幅:
《圣塞巴斯蒂安》()圭多·雷尼
少有画家如此频繁、大量地以圣塞巴斯蒂安为题进行创作。雷尼的风格受到卡拉瓦乔主义和自然主义的重要影响。根据同代人所言,雷尼本人很接近于无性恋,他畏惧女性、不好女色3,但和卡拉瓦乔不同,他也从未有过男性情人。人们评价他具有雌雄同体的气质(据说,他还曾在一幅壁画中把自己刻画成美丽的女人的形象)。
这种双性气质无疑表现在了他的圣塞巴斯蒂安画作中——圣徒的眼神清澈无辜,脸庞染着红霞、极明显地带有女性化的柔美,身姿扭动的角度哪怕用“婉媚”一词加以形容也不觉不恰。
圭多·雷尼的另一件《圣塞巴斯蒂安》(-)
赫希菲尔德论及性倒错者4特别喜好的绘画雕刻时,把“圣塞巴斯蒂安的绘画”排在第一位,对此三岛解释说“性倒错者,其性倒错的冲动和施虐狂的冲动大多是错综交织在一起,难以区分的。”
何谓施虐的冲动?这是三岛将圣徒之痛加于自我的“共情”在起作用,还是由观察作为客体的圣塞巴斯蒂安而生发出的爱?
“性虐”这个词可拆分成“性”和“虐”。“性”的意味是艺术家主观加诸其上的概念——不仅源于对自己性偏好的炽烈的表达欲,同时,圣塞巴斯蒂安在文艺复兴时期被涂抹上肉欲的色彩,也是一种商业化的需求。上流社会贵族中,不乏好将裸体画作摆在卧房之内者,而圣塞巴斯蒂安作为殉教者的身份,让其裸体变得“合乎道德”了起来。不仅关于他的画作被富人们竞相购买,他本身也成为了除耶稣以外少数被当时宗教社会所接受的裸体艺术形象。(然而仔细想想,塞巴斯蒂安在三世纪接受处刑时是很仓促的,行刑者们其实完全没有剥光他衣服的必要。)
相比之下,受“虐”则是圣塞巴斯蒂安固有的属性,毕竟经受痛苦才是殉道的必然过程。这一过程体现在圣塞巴斯蒂安身上最显著之处,私以为并非箭,而是绑缚。箭的数量、角度,是否画出人体的流血,这些画家皆可自行拿捏、随心所欲;然而身体的桎梏却必不可少——尽管那只是必要的形式。反剪的双手,悬吊的双手,怎样缚其实不重要,能否真的绑住也无所谓;黑峻峻的树木,蒙了烟尘的石柱,用什么作刑台都可以。但若缺少某种束缚,塞巴斯蒂安的形象就瞬间轻佻无趣,失去了辨识度。
也有一些并非站立构图的作品。如这幅:《将死的圣塞巴斯蒂安》()弗朗西斯-哈维尔·法布尔
弗拉·巴尔托洛梅奥为圣马可教堂绘制的《圣塞巴斯蒂安》(),画中人未受缚,姿态自由奔放、遮蔽甚少。这幅画所表现的裸体形象遭到教会激烈的反对,并且因为“它让女性教徒的视线过于炽热”最终被教堂移除了。
三岛由纪夫对圣塞巴斯蒂安的痴迷,还有另外一层:据他自己的描述,那是热爱死亡本身。《假面的告白》中,三岛说自己对“死亡、黑夜和热血”满怀向往,着迷于追求人身上的“悲剧性”,并且,无法逃离“‘被杀王子’的幻影”对他执拗的纠缠。幼年时看到的童话插图中,王子英勇走向死亡的命运深深蛊惑他的魂魄。
“王子”随着三岛的成长幻化成了圣塞巴斯蒂安——那个于死亡的前一页上,被画布和油彩永远封存、制成了标本的圣徒。
真正的圣塞巴斯蒂安在乱棒下殒命的场面,似乎已被历史忘却——与其说忘却,倒不如说刻意忽略。毕竟被乱棍打死,看起来无论如何都不会太美。
正如前面所述,圣塞巴斯蒂安并不死于箭。箭是预告,是死亡的模拟,正像塞巴斯蒂安的形象本身亦充满模仿的因素。传说中从未仔细描述他伤口的位置,但许多画家即使只留给塞巴斯蒂安一两支箭,也常常不吝啬那一支插在肋间的箭头。一来如此绘画更美观,二来这也可以理解成是对耶稣右肋上圣痕5的模仿。此外,圣塞巴斯蒂安死后再生,似也能与教义中耶稣的复活相照应。
晚年时,三岛自己又对圣塞巴斯蒂安之“死”进行了模仿。他完成了“肉体改造”,一改以往的羸弱,练就了一副健美的身材。他“终于将这个身体弄到手之后,就像得到了新玩具的孩子一样兴奋,想到处去卖弄,到处去炫耀……”于是就有了和日本摄影师筱山纪信合作创作的写真集《男人之死》。拍摄从年开始,前后跨度近一年。其中最著名的便是这一张:三岛将自己的两腕以绳结捆绑起来,高悬于树上,像雷尼的塞巴斯蒂安那样,扬颈收腹,仰视苍空。三支箭将他射穿。
筱山纪信拍摄的三岛由纪夫
近些年的作家中,有人将圣塞巴斯蒂安称作“完美的死亡预备者”6,我想这一评价若给予三岛,也颇为合适。
年11月25日,距离拍下最后一张照片仅仅才过去一周。三岛带领4名盾会7成员闯入自卫队总监部发表演说,但是无人响应。他额头系上写着“七生报国”字样的头巾,持着短刀对腹部刺下,表演了一场震惊举国的自杀。
后来筱山纪信在节目中再谈到三岛,说:“虽然在拍摄时他总是将死的话题挂在嘴边,但我完全没想到三岛真的选择了死亡。”
从童年时就乐于幻想自己被杀死的情景、而又偏偏比别人对死亡抱有更强烈的恐惧的三岛,以肉身拥抱箭矢、把自己献祭给死神的三岛,终于得到了类似于圣塞巴斯蒂安的永恒一刻。
对于三岛,圣塞巴斯蒂安究竟是美学的意味更多,还是性的吸引更多,这也许就要看读者各自的想法了。无论怎样,历史的进程中,圣塞巴斯蒂安倒也确实阴差阳错地成为了经典的同志崇拜符号。有人说这还是要追溯回文艺复兴时期——尽管当时基督教的法律仍然严苛,也还是无法阻止那些从古希腊文化中获取养分的人文巨匠们,背地里大行断袖之风。
此种情况下,圣塞巴斯蒂安又是如何那么特别地成为了表现同性爱的意象,除却那个民间关于戴克里先的传言,我认为主要还有以下几点。
一是他本身健硕的阳刚美。这点大可不必再赘述。除瘟疫的保佑神以外,圣塞巴斯蒂安还被看作是运动员和战士的庇护者。
二是他和箭矢的紧密联系。当代性学家多认为,文艺作品中,“捅伤”“刺伤”之类的动作常被赋予隐晦的性暗示意味,并且作为性交的替代品出现。从这种角度看来,圣塞巴斯蒂安身上插入的箭,像极了充满支配欲和征服性的男性阳具;而他的受刑像极了一场奸淫。历史传说中笃信基督的塞巴斯蒂安明明既无声色绯闻,也没有一位爱人,纯洁得如同处子;刺穿如此纯粹的美,是极具宗教意义的。
三是他身为近卫队长的身份惹人遐想。古希腊对男性之爱的鼓励,很大程度上体现在行伍之中。柏拉图在《会饮篇》中写道:“要是全由有情人和情伴8来组建一个城邦或一支军队,他们就会把自己的生活治理得再好不过了。”古希腊城邦底比斯在公元前年创建了一支精锐部队“底比斯圣军”,由对男同性恋爱侣组成。他们为与爱人并肩作战到最后一刻,比普通的军队更加勇猛、忠诚,在留克特拉战役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真实历史上塞巴斯蒂安的军中生活并无实证,只能任由人想象了。《假面的告白》中这样描写:
大强度练兵间歇时,头盔上的百合花9随着他英武的长发优雅地低垂,姿态宛如天鹅的颈项。
……迫于繁忙的军务,塞巴斯蒂安在拂晓时分就从床上一跃而起。……梦中,不祥之兆的鸟雀成群停落在他的胸脯上,张开的翅膀遮住了他的嘴。……他站立在窗边,边穿戴铿锵作响的盔甲,边眺望远方包围着神殿的森林上空,北斗星座正在沉落。
这样的情境,文艺复兴画家们鲜有将其用于圣塞巴斯蒂安主题作品中的。然而人们对这位圣徒的热情并未因为时代的变化就有所消退。年英国导演德里克·贾曼拍摄的电影《塞巴斯蒂安》,就详细地呈现了幻想中这位近卫队长官的生活。
贾曼很罕见地全程使用了拉丁语对白拍摄,剧情大多是杜撰的故事,镜头却极富古希腊式的典雅美感。电影中,塞巴斯蒂安和其他五名士兵一起被流放至沙漠。虔诚的塞巴斯蒂安一心只爱神,而长官却千方百计想要占有他,最终因爱而不得,下了杀手。
沙漠风景荒凉苍莽,由大色块的深蓝和藤黄拼接而成。铠甲上银光明灭,湖面泛着清波,年轻男子们或着麻布长袍,或披皮革,信步游荡着。每当夜幕降临,暧昧的气氛便在空气中浮动。影片中大量充斥着男性的裸体,散发出旖旎香艳的软色情气息。士兵们在沙地上练习战斗、围捕野猪、放牧、洗浴、戏水……很难想象这些活动都是在桃色的基调之中进行的。
《塞巴斯蒂安》剧照
导演显然有着极重的古希腊情结,并将一些不相关的神话意象也奇妙地点缀了进来。塞巴斯蒂安坐于水洼一侧,对自己的倒影吟诗,不能不让人联想到美少年纳喀索斯。传闻中那喀索斯对自己的影子爱慕不已,溺于水中,化为了一株水仙花。
望着倒影的塞巴斯蒂安
纳喀索斯贪恋自身的美,塞巴斯蒂安却全然未发现自身的美。他仰望着天堂的双眸是那般坚定,从不舍得低下头来看一眼自己淌着鲜血的箭伤;他对不可亵渎的神爱得那样深切,以至于不曾在心中留一角赐给自己的怜悯。
过去,油画里的圣塞巴斯蒂安多为极其静穆的形象,贾曼的电影让我们难得地看到了动态的处刑。一支支箭矢飞入那古铜色城墙般的躯体,暗红的溪流蜿蜒而下,汇聚成一道,接着又泛滥奔涌。塞巴斯蒂安昂起的头渐渐低垂了。无声的长镜头中,痛苦被无限拉长,几乎要永久地延伸下去。
塞巴斯蒂安之死
从古至今,圣塞巴斯蒂安被无数人加以解读、创造、重塑,他的主题留下了浩繁的文艺作品,也成为了宗教画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家们永不疲于描绘圣塞巴斯蒂安,希冀着通过创作,将神的意志体现于人世,将刹那间的美保存下来。
然而,如此这般,圣塞巴斯蒂安的轮廓就清晰起来了吗?恐怕未必。塞巴斯蒂安被人任意打扮,穿上了色欲的华服,又戴上保护神的礼帽……
真正的圣塞巴斯蒂安被掩饰了。可真正的圣塞巴斯蒂安又在哪里呢?真正的圣塞巴斯蒂安大概已经消失了。他侍奉唯一真神而死,却没有察觉跪下来亲吻神明脚尖的自己,竟是那样一尘不染、洁净无瑕。
塞巴斯蒂安是投入了水中的石片,他在历史中沉下,被污浊的浪涛埋葬。然而水面上他激起的灵感与美的涟漪,却是一圈圈扩散开来,久久荡漾不息。
之后,我找到了那帧画,那张圣塞巴斯蒂安殉教图。从北海道回国之后的深秋,我在某家书店邂逅了一本收录有卡拉瓦乔全部现存作品信息的画册。从第一页翻起,最终见到那张油画以极小的尺寸印在书页一角,我顿时激动得难以言表,差点就要旁若无人地大叫起来了。
下有英文简介。我才知道在美术馆见到的原是复制品,卡拉瓦乔的真迹早已遗失。
画册中的一页
这么看来,也许果然还是没找到呢。也许,整个世界都再不会找到这幅画了。
初秋的雨仍然淅淅沥沥,下个不停。雨夜,我的梦总氤氲着潮湿的水汽;梦境远处无垠的灰色之中,永恒地立着一个男子。
《圣塞巴斯蒂安》米开朗基罗·卡拉瓦乔
注:
1古希腊神话中的大地女神。
2射精的意思。此处沿用三岛原文中的说法。
3雷尼一直和母亲生活到55岁。据说在母亲死后,雷尼拒绝让任何女人进他的房子,或让女性的衣物碰到他自己的衣物。
4性变态的旧称,此处沿用三岛原文中的说法。当时,同性恋还被划为精神病的范畴。
5耶稣右肋下的伤口是著名的“圣五伤”之一。在耶稣受难当日,罗马人为证明他已死亡,便拿枪扎了他的右肋。
6见WolfgangTillmansSaintSebastian:OrASplendidReadinessForDeath
7盾会是三岛年组织的私人武装。他声称要保存日本传统的武士道精神、保卫天皇,志在推翻否定日本拥有军队的宪法,使自卫队成为真的军队。
8城邦时代,克里特岛流行一种男子“诱拐”少年的风俗,并逐渐形成了制度。他们称这种关系为“爱者”和“被爱者”。成年男子会与男孩共同生活、训练,传授给他知识和对国家的忠诚感,将其培养为一名合格的公民。此处的“有情人”和“情伴”大体上说的也是这种关系。
9百合花也是古代欧洲指代男色的意象,源于古希腊神话中美少年希亚辛萨斯的故事。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