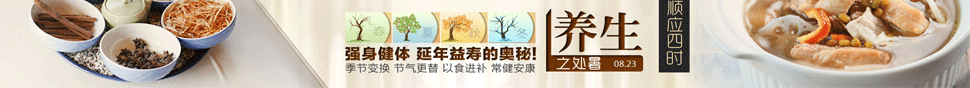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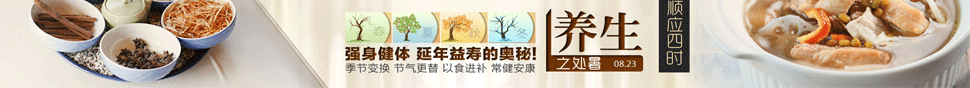
海东文化
图片选自网络
首届吴伯箫散文奖投稿邮箱:jnhdwh
.柴园是我故乡,也是我童年乐土。
柴园背靠一片弧形矮山,中高侧低,像一把椅子,就叫椅山。椅山长了很多杂树,有继木、石茶等落叶灌木,也有松柏、香樟和水杉等常青乔木,赤橙黄绿青蓝紫,一年四季不断变换颜色,绿意袭人。据说这是风水山,禁止砍柴和放牧,只允许老弱妇孺进山拾捡枯枝断树煮食;村前有条大河,从上游笔直流来,绕村半周到下游又笔直流去,恰好与椅山构成一个括号,把村庄围在其中。某年,有游方先生经此,观之击掌叫好:“山环水绕,风水宝地。”
山与村之间是阡陌,肥田沃土,种植谷、粟、高梁、小麦。上游两架木制水车,日夜不停碌碌辚转,灌溉作物;下游一个水碾磨坊,一个水碾油坊,加工制作粮油。
山是青山,水是碧水,青波碧浪,清彻见底,能看见水底五色河石和摇曳水草,鱼虾在草石间来回嘻戏;河岸上有数百年之久的香樟、皂角、康木和水柳,长满苔衣和藤萝,常有村民在树上帖了红纸,书云:“天皇皇,地皇皇,柴园有个夜哭郎。过路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光。”或在树下摆了三牲果酒,将雏磕头拜祭,随将子女取名樟树保或柳树宝。
岸边有青石铺砌汲水埠头,一级级下到河边,又从河边伸出一块石板至河心,利汲水浣衣濯足之便。晨昏之际,妇孺梆梆捣衣之声不绝于耳。夏夜,村民饭后移一张竹床或铺一块禾席在岸上纳凉,燃一束艾草,坐看水月,静听虫吟,闲聊桑麻,任河水汤汤流远。
河边拴着木船和竹排,利渡水和捕捞之用。夏季,一场大水涨过,鲤鱼、草鱼和鲢鱼从下游溯河而上,在浅滩上集结,柴园人便划了木船和竹排撒网捕鱼。下河赶鸟人也来了,他们往往是夜里来,弯头竹排上装了汽灯,载了鸬鹚(鸟),在河面上排开阵势,用竹篙啪啪击水,嘴里嗬嗬吼着号子,将鱼驱至某个区域,驱使鸬鹚下水捕鱼。
柴园有很多青瓦灰墙老房子。瓦片生了青苔,瓦槽里长出野麦子和狗尾巴草,麻雀子啄食麦粒后顺便在里面筑巢,引来夜鼠捉雀。猫又去捉鼠,所以瓦片总是凌乱,屋里人也不得安宁,又漏雨又噪扰,屋主人也就是我父辈们每年秋天农闲时节都要请捡瓦师傅上房盖新瓦。捡瓦师傅不仅捡到雀蛋,还会捡去包在老房大梁上的铜钱。这个秘密只有我们小孩知道,因为捡瓦师傅上房时我们就在房下抬头看。捡瓦师傅下房了,雀蛋分给我们,铜钱揣他兜里了。也许父辈也知道这个秘密,但他们心照不宣,照样招待捡瓦师傅吃饭,打发工钱,约他们下次再来捡瓦。有时梁上也会掉下两个绿锈红斑铜钱,我们就偷偷捡起去换丁丁糖吃。也不知为什么,每当老房子需要捡瓦时,货郎就在村里出现了。他们挑着货担,一头装了针头、丝钱、洋红、顶针、鞋拔、锥子,一头装了叮叮糖一一麦芽糖和蔗糖混熬的糖,琥珀色,坚硬,脆甜,用一把小铜锤叮叮敲打錾子,一小块一小块錾开成豆丁样,丁丁糖的称呼就是由这声音和形状来的。
一个铜钱换一小块,一个银豪换两小块,若是一块袁大头或是一块龙洋,就能换一大块。换完他们就走,咣啷咣啷摇着拔浪鼓健步如飞,即使后面追着一大群流口水的小把戏也决不停留,因为银豪和光洋在柴园是奢侈物,都是小孩从老太爷老太太笼箱底偷出来的,怕大人发现生事。然而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柴园的大人是不会责怪他们的,只会责怪自已孩子———在孩子小手上拍几下以示训诫,然后锁好笼箱,没事了。货郎若是换不到铜钱和银洋,就把挑子搁在一家屋门口,坐在石凳上和妇女们拉家常,吃她们打的油茶,介绍自已的丝线如何坚韧光滑,绣出图案如何鲜艳生动;顶针如何结实耐用,不伤手指。妇女们经不住他说,就抓一把炒米、撮一勺豆豉换几束丝线一个顶针,打发他走了,不耽误他到别村做生意。
货郎走了,冬天来了。一个寒冷早晨,有人推门出屋,被漫山遍野白霜晃得睁不开眼睛,禁不住啊呀一声惊叹,冬天来了。
俗话说,落雪落雨,烧柴吃米。在大雪封山的冬天,柴火带给柴园人温暖和欢乐。柴园人家的火堂都是在地上嵌一个正方形砖框,把一个烧水煮饭的三脚铁撑架围在中间。火堂四面用杉木板镶嵌壁墙,不留窗,柴烟从屋瓦空隙散发,光线则从屋顶亮瓦射进,既温暖又明亮。火堂头上是木楼,上面有粮仓和杂物,堆着备用木柴;下面是四根铁线吊起的木架,上面也放着木柴,烧火时随手取下来。吊架下面挂腊肉,有猪、羊、牛、狗、鸡、鸭、鱼肉。腊肉以为猪肉为多。柴园人有杀年猪习俗。年前,将平时煮猪食的大铁锅装水烧热,请来屠夫,用铁钩把猪鼻勾住,一绳子拉到杀场。屠夫都是膘肥体壮大汉,嘴叼杀刀,横眉竖眼,猪一见瑟瑟颤抖四肢发软。屠夫趁机大吼一声,一脚把猪踹倒,其他人帮忙按住。屠夫右脚踏住猪身,左手捏住猪嘴,右手从嘴里取下尖刀,嗤一声插进猪喉腔。猪抽搐哀鸣一阵,呜呼哀哉。
年猪杀好,主家通知亲戚们来吃“骨头”。为什么不叫吃猪肉而叫吃骨头呢?这个说法没法考证。剩下猪肉就用盐渍了,挂在吊架上,一直要吃到第二年冬天。来客时,随手取下一块,用灰水洗去烟垢,配酸辣料爆炒,喝瓦壶烧热的杂粮酒,一醉方休。
整个冬天,柴园人基本上不离开火堂。早上起来,用铁夹把火堂灰堆扒开,仍有未熄火炭,这是主人昨晚临睡前团的。在火炭上放一些细柴,用吹火筒吹燃,火堂就又开始了它一天热烈而欢乐的燃烧。
柴园人早餐都喝油茶吃糍粑。油茶的主食是炒米。霜降期间,天气晴朗,阳光明媚,柴园人把糯米放在大黄桶里蒸熟,撒在竹垫上晒干。讲究一些的人,还会用植物汁染出一些红绿颜色,叫米花。食用时,在茶锅里放进茶油,把米花翻炒到膨胀发白浓香扑鼻,这就是炒米。泡炒米的汤要用很多佐料,如生姜、花生、胡椒、茶叶、豆豉、蒜米,用木棰捣烂,井水煮沸。这时,放在火堂边铁丝架上的糍粑也烤熟了,吃起来香软可口。作糍粑的主料也是糯米,也是在大黄桶里蒸熟,然后舀到石碓里,趁热用木棰捣烂,作成一个个圆饼,用木戳印上喜鹊登枝、福寿双全等吉祥图案,喜庆如是。
柴园的冬天最热闹的日子是从腊月到元宵这段时间。家家办年货,户户放鞭炮,跑草龙,舞狮子,唱彩调,皆大欢喜。
水使人柔情,火使人热烈,柴园的整个冬天都在熊熊燃烧着。
崔久龙:日照市东港区迎宾路29号(酒厂家属院)
欢迎加入山东省散文学会!
山东省散文学会成立于年,是由山东省作家协会主管、山东省社科联业务指导,在山东省民政厅登记注册的省一级法人学术社会团体。
欢迎广大山东散文作家(含山东籍、在山东工作)和热心编辑组织工作的朋友加入学会共同推动山东散文事业繁荣发展。会员电子表请登录
本文编辑:佚名
转载请注明出地址 http://www.yizhijiana.com/yzjtx/1273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