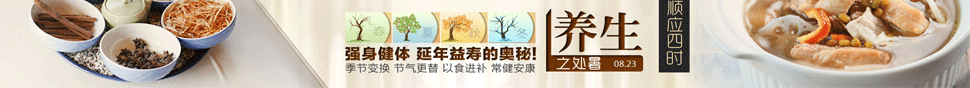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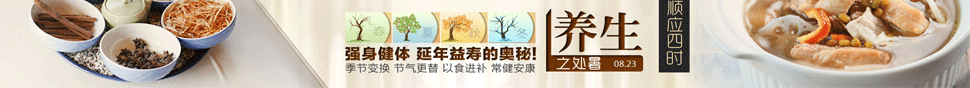
第64期
周末的电话粥
青岛十五中马冬勤
每逢周末,总要煲两锅电话粥,一是和母亲,一是和儿子。
照例是琐琐碎碎,照例是黏黏糊糊。母亲先说自己识字更多了,都可以看着养生手册做饭了;接着说这些天体重猛增,过去的衣服都扣不上扣子了;又说自己做了一坛子的西瓜酱,味道好极了,等我过年回家时可以带些回来;还说她腌的韭花味道很好,已经用玻璃罐盛了放起来,留着我们过年回家吃……最后还是再三地嘱咐我,要认真做饭吃饭;工作不要逞强争胜;星期天多休息,别没完没了收拾家;我和你爸都挺好,不要记挂……我倾听者,附和着,应答者,电话那头的声音平和安乐,让我觉得整个世界都不急不躁,安详美好;那一点一点的关照惦记,让我觉得这世界上有一个角落只属于我,我可以随时回去,可以行囊饱满,也可以两手空空;在那里,没有责备和苛求,只有接纳和包容;在那里,我总是好的,总是对的,总是至关重要的。
晚上窝在床上看书,听到窗外北风呼啸,阿伴说:“该和小弟通个电话了,不知他那里冷了没有。”于是拨通电话,那头传来儿子爽朗的声音,立即判断:心情不错,肯定是实验顺利!果然,儿子说,在研三师兄的帮助下,对实验进行了全面的观照规划,现在觉得有条有理,信心十足。接着谈导师宛如黑脸凶神,见面就要骂人,总有一天“誓将去汝”,然后再“衣锦还乡”,让他也有机会惭愧“悔不当初……”接着又谈佛教主张“人人皆可成佛”,比较“亲民”,不像其他宗教给人一种居高临下的威压;接着又谈将来安家,又谈天冷加衣,又谈一日三餐……忽然儿子郑重其事地提出一个问题:知道中国第五大菜系是什么吗?我们面面相觑,他那里哈哈大笑:“第五菜系是食堂菜,清汤寡水;至尊菜系是妈妈菜,百吃不厌……”我凑凑合合捯饬的饭菜在儿子那里总是无上美味,作为一“吃货”,他的乡愁永远和“炖鸡”“排骨”“馄饨”“蒸饺”这些“家的味道”连在一起。听着儿子东拉西扯,顿觉世界在延展,生活在延展,生命在延展,种种期待、念想都有了一个实实在在的着落。好像有一个长长的镜头层层拉近,茫茫天地间有一个海滨小城,小城密密的楼群里有一间弥满灯光的小屋,小屋里有一对牵肠挂肚的父母,父母的心坎上有一个老也长不大、需要千叮万嘱的儿子。
曾经看到一段话说,上有老下有小,是人生的幸福,我正深深地体会着这样的幸福。上有老,我可以作为孩子,让一颗心有所归依;下有小,我可以作为母亲,让一颗心有处安放。所以,每周的电话粥,我从来都不计成本,任由它小灶文火,慢慢煲,慢慢煲……
不要让他老去!
——给父亲
温州永嘉县教研室肖培东
我搀着父亲,像搀着冬天里的一棵老树。冬天的苍白与惨淡如约而至,父亲也在这个季节应景似地老去,从医院到家只有很小的一段路,我搀着父亲,却走了好一阵子。偶尔我会捏捏父亲的手臂,没有孩提时代我感受到的那份生气与雄壮,肉是散散的,就像身边一树树下垂的枝条,抖不起春天的蓬勃。父亲,我的父亲,无法挽回的衰老了。
父亲,会在这样的行走中喃喃自语,说着眼前的一丛衰草,说着脚边的一叶枯败,仿佛在他的自言自语中,它们都会重新泛起生命的绿色。然后,医院看病花费了多少钱,迷茫的眼睛里总是流露出一抹愧疚,为自己的身体给家庭带来的经济损失,为自己的药费给我带来的心灵疼痛。父亲,永远不知道,医院的时候我是多么高兴,我搀你的手其实是想搀住你衰老的时光,把你拽回青春拽回力量。我微微地笑着,而父亲总是一脸内疚,仿佛是他,带来了这个冬天,是他,驱走了那片春光。我望了望父亲,很真诚地笑着,即使你的步伐是如此缓慢,我也觉得你是在努力赶上我们家庭欢乐的列车。父亲,你知道吗?没有什么比你还能和我们一起行走更让人愉快的,即使那身影,是像深秋时光里的一道艰难的蹒跚。
“东,爸爸要是走了,你心痛不?”父亲总喜欢这样问我,这次,多了一份认真。
“爸,怎么可能呢?你要活到九十九的。”我故作玩笑,逗着我的老父亲,“你要走了,谁给我包粽子,谁给我做麦饼……”父亲,我的父亲是笑了,满脸的皱纹缓缓疏散,然后又重新聚拢,怎么看都像是一把秋叶无序地散落在大地上,又被风吹得挤在一边。我又看看远处的大地,在初冬的惨白中裸露着所有的空旷,默默承载着流动的时光、更迭的人群、以及由此而繁衍的喜怒哀乐。父亲就是这大地上一棵树,绿过,黄过,茂盛过,又稀疏过,就这样一季一季地生活着……
时间只负责流过,不负责你的成长与苍老。当我能挺起胸膛大步走向远方的时候,我的父亲却猝不及防地老去着。我愧疚地搀着父亲,像搀着冬天里的一棵老树。
风吹起了父亲的头发,白色的,诠释着忧伤的衰老。其实,父亲,儿子的头发也开始白了,只是我会很好地掩饰着,不想让你看到我的艰难而有所忧伤。但是,我知道,在我小时候的时候,父亲,还有我的母亲,那一头的黑发是很顽强地泼洒在岁月里的。我点数着父亲的白发:这一根,是为了我瘦弱的身体而白的,我不争气的体格总让你们担忧;这一根,是为姐姐的前途而白的,叛逆又追求自由的姐姐从来都是你们无尽的心事;这一根,是为我的高考而白的,谁让我考语文的时候晕倒在考场呢;这一根,是为六六不肯吃饭而白的,六六一直就是你们的心头肉,一天看不到六六你们就无限地压抑……父亲,我的父亲,我以为我长大了,赚钱了,可以为你们披上一件温暖的外套,穿上一双软软的鞋了,你们舒心的微笑就永远了,可谁知,是父母,你们就有说不尽的忧伤,是长辈,你们就有道不明的苦闷,是吗,我的父亲?
我整理一下父亲的衣角,搀着父亲走在回家的路上。
父亲穿上了我给的毛衣,不是很协调,但是很开心。我努力看着父亲的脸,想把这个冬天的印象都留在我的心底。在我去成都去重庆的日子里,父亲骑着小三轮车摔了下来,他原本一只眼睛就睁不开,加上路上有凹陷,说摔就摔了。他瞒着我,不让家里人告诉我,等我回家才看到我医院里挂着盐水。脸上一片乌青,眼睛周围,嘴角,更可怕的是在煤矿里受伤的鼻梁又一次断裂了,人浮肿着,脸色憔悴。记忆里,这种惨象就是我还在长兴读书的时候父亲在矿井里受伤的再版,那时的天真冷,北风呼啸着,整个矿井都在颤抖。我想起二十多年前的绑着绷带的父亲,再看看眼前衰老了却又一次鼻青脸肿的父亲,我的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听说,流了很多的血,听说,父亲摔成这样子后还是自己骑车回家的,那条路上,滴滴点点,都是父亲的血……那个时候,我还在外地意气风发地讲课,激情四溢;而我的父亲,却倒在家乡的路上,艰难地起身,然后带着满脸的血孤独地骑车,还按时在“东,外面冷不?”父亲,我的父亲!
我搀着父亲,走在风里,医院落在了我们的身后。
这几年,医院的缘分越来越深。脑血管动脉瘤手术,心脏病,鼻骨断裂……像父亲侍弄了一辈子的菜园,绿了一茬又被割了,绿了一茬又被割了。我心痛地望着父亲,父亲却带着浓浓的鼻音挣扎着说“不疼了”,听这句话时,父亲在困苦的岁月里挣扎的身影历历在目。我深深地凝视着我的父亲,看着这个被岁月风霜雕琢得越来越坎坷的丑陋的慈爱的我的父亲,我担心自己一晃眼,父亲就会倏然消逝,化成这荒山野草间一堆冷冷的黄土。我给父亲敲了敲背,那背,不再硬朗,开始像弯弓。也许在父亲的眼里,我就是一支箭,我要闯向远方,父亲他就要弯成佝偻,可父亲,你也不能弯成我满腔的愧疚啊。
到家了,父亲不用我搀着就进了门。我看着父亲欢天喜地地走进那熟悉的家,看着他很快就用他那温暖厚实却很显粗糙的手抚摸起他的锅瓦瓢盆,像久违了的亲人。我想起遥远的童年,父亲和我们那一间小小的平房,心里一阵酸楚。
祈祷着,时间啊,请慢些吧,不要再让他老去!
我那一刻,我的眼睛模糊了。
校本课程之“前言”
青岛十五中王绯霞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知识不仅仅在斗室之中,不仅仅在薄薄的书本上,也不仅仅是老师站在三尺讲台上的传道授业。天光云影中有字,清风明月处有诗,涛声阵阵里有曲,一砖一瓦里有画,小巷深处有杏花。坎井之蛙只能坐井观天,要开阔学生的视野,必须引领学生到自然中去,到社会中去,到无字句处读书。
青岛作为一个年轻的城市,既有大自然赐予的碧海蓝天,有青岛人亲手打造的红瓦绿树,更有大师们留下的深厚的文化底蕴,所有这些,都静静地等在一隅,等待我们去开掘,去享受。比如天后宫的民俗文化,文化名人一条街,中山公园的樱花,百花苑的雕塑……
那是一个几千年前孔老夫子早已描绘过的画面:暮春三月,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人在青岛,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文化之旅,那是紧张的教学和学习过程中的一次快乐之旅,沐着春风,人在画中游,雨中游,和谐,快乐,轻松,自由,心灵便来了一次洗礼,干净,清澈,忽然之间,便撞了王摩诘的意境: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犹记那个午后,师生一行五十几人,中山公园一游,只见樱花如雪,人流如织,蛙鸣阵阵,杨柳依依,为之迷醉,流连难返。如锦似缎的郁金香花前,一男生低头俯身向花而嗅,见之不觉莞尔: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忽而细雨蒙蒙,无奈踏上归途,众人俱坐公交,唯有两男生选择步行。车上却见二人持伞未开,安步当车,冒雨踽踽行于木栈道之上,面不改色,谈笑风生,又不觉莞尔:此情此景,何其熟悉,魏晋风度,莫非如此?
一场说走就走的文化之旅,任性,洒脱,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花一草,一砖一瓦,一颦一笑,亦足以极视听之娱,岂不乐哉!
老师,请把枪口抬高一厘米
江苏张家港高级中学王开东
年2月,柏林墙倒塌两年后,守墙卫兵亨里奇受到了审判。
原因是在柏林墙倒塌前,27岁的他射杀了一位企图翻墙而过的青年。
亨里奇的辩护律师为他辩护说:“亨里奇作为军人,他仅仅是在执行命令而已,他别无选择,罪不在他。”
然而法官西奥多?赛德尔却不这么认为:“作为军人,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冲突之时,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尊重生命,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
因此最后法官判处亨里奇入狱三年,而且不许假释。
之所以想起这个故事,乃是因为南通初二学生的这一篇零分作文,刺痛了我。
孩子有什么错?尽管有一些偏激,但他说了内心里最真实的话。他有自己的观点,能够引经据典论证,文采也还不错。重要的是,这篇文章,让我们老师感到疼了,感到痛了,引发我们思考了。
老实说,这样的文章并不多见。
至少他在思考,他在表达,他在困惑,他在愤怒。他很清楚这样写的命运;但在一次次的挣扎思考之后,他终于勇敢地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我不能沉默,我必须要说,我必须听从自己内心的抉择。”
这是一个多么真性情的孩子!
在现在的教育体制下,这样的孩子是多么稀缺啊。
钱理群先生说,北大里面的天子骄子绝大多数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遑论其他?
我们见过太多的,无病呻吟的,风花雪月假大空的文章了。
不客气的说,这些孩子身上也有我们教育者的影子,我们培养的都是些什么人啊。有耳朵却不会聆听;有嘴巴却不会说自己的话,言不由衷,言不及义;有眼睛却看不到美好的内容,对美好无动于衷,甚至与美好绝缘了;有脑袋却不会思考,自己的脑袋不过是别人的跑马场……从来,没有想到过,我是谁?我是一个大写的人,我很重要,我要表达,我有自己的观点和权力,我不高兴!
一方面要求学生写出真情实感,写出自己的独到认识;一方面又限制学生,只允许戴上玫瑰色的眼镜,只允许看到生活中那些不存在的涂脂抹粉。
文如其人,这些恶劣的文风,自然潜移默化地影响这些孩子,久而久之,孩子们就会变成假大空的虚伪的人,他们察言观色,对成人世界的规则烂熟于心,并且很快就与社会达成了谅解,与社会沆瀣一气,这里都有我们的一份“功劳”。
一旦孩子看到皇帝的新装了,说那个皇帝是光着屁股的,哪怕我们在心里骂过一万次皇帝;但这个时候,我们内心中的正义感粉墨登场了,我们挥舞起剪刀,担当起辛勤的园丁,剪刀过处,断肢残臂,血流成河。然后,所有的孩子,整齐划一了,一个眼睛看物,一个声音说话,一个鼻孔出气,只有两个眼珠间或一轮,才知道是一个活物。
一年又一年,我们一大批一大批标准化的零件出场了,教育又取得了特大的丰收!
只是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之下,教育一片荒芜,教育没有了,人不见了。
在一个庞大的机器下,在指挥棒和威权下,作为教师个体,有时候的确是渺小的,甚至微不足道。如同《肖申克的救赎》中所言,对于恶劣的体制,我们起先讨厌它,后来,慢慢适应它,最后,我们依赖它,离不开它。最后的最后,就是我们成了它肌体的一部分。在一个班级之中,在我们的笔下,我们就是体制。
不要以为,大家都在做,体制要求我们这样做,我们就没有错。鲁迅曾经愤激的反问:“从来如此,就是对的吗?”我们勤勤恳恳,却诲人不倦,我们都犯有平庸无奇的恶。
要知道,即使在最黑暗的核心地带,也有光明的种子。被誉为“俄罗斯良心”的索尔仁尼琴就曾自豪地宣称:“我从未背叛过自己的良知。”
作为教师,在体制和良心之间,我们也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好一个孩子说真话的勇气,把枪口抬高一厘米!
在《古拉格群岛》里有这样一段话:
“命运只许我用压弯的、几乎要折断的脊背从狱中年代里驮出一条这样的经验:人是怎样变成恶人和怎样变成好人的。在少年得志的迷醉中我曾觉得自己是不会有过失的,因而我残忍。当大权在握时我曾是一名刽子手和压迫者。在我穷凶极恶的时候我确信我在做好事,我有头头是道的理由。只有当我躺在牢狱里霉烂的麦秸上的时候心里才感觉到善的第一次蠕动。我逐渐发现善与恶的界线并不在国家与国家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而是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穿过,在一切人的心中穿过。这条线在移动,它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摆动;连被恶占据了的心中也保持着一小块善的阵地。”
这一块善的阵地是什么?首先是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然后,就是把潮水搁浅在沙滩的小鱼,一条条的扔进海里去。
当我们挣扎着,一次又一次的把一条条小鱼扔进海里去,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拯救所有的小鱼;但我们也知道,我们所扔的每一条小鱼都在乎。他们将与自由的大海融为一体,从而成为这个体制的漏网之鱼,并进而为我们这个民族保留一线希望。
我要这样生活
温州永嘉县教研室肖培东
(原载于《人民教育》年第9期)
请别奢望我会把所有的时间都给了学校、给了学生。
那不是教育。
至少不是我要的教育。
下课了,改完作业了,备好课了,走出校园,我就该走向教育工作时间以外的我。我很认真地工作,我很讲效率地教书,就是为了我能赢得更多的属于我自己的时间。阳光照耀在肩上,我会暖暖地走向原野,走向森林。我看着小鸟在空中轻捷地划过痕迹,我看着小草在土地的呓语声中悄悄萌芽,所有的小虫子都和我一起轻步飞扬,我就把春天留在我的眼睛里。雪花倏忽钻进我的脖子,我会伸出手接过下一朵菱形或花瓣形的晶莹,和孩子一起等待着空中的下一个柔软的飘落,把足迹留在雪白的大地上。当哈出的热气遁形于苍茫冷色的天宇间,我就把冬天融在我的希望里。
然后,我要阅读,读留在我枕边的智慧,与哲人对话,与思想碰撞。当然,我不一定必须读教育书籍,也不一定要写成读后感或抄成读书笔记,我也看看休闲的,一个笑话一个幽默都足以让我一天变得轻松愉快。
然后,我一定会听我的音乐。在如堆的唱片里,我会找出几张。或是尼古拉·安杰罗斯柔情浪漫舒爽甜蜜的吉他独奏《安娜小笺》及《人们的梦》,六弦音符在指尖划出一片惬意的天空,此时,震颤的不仅是琴弦,而是心。或者是KennyG优雅的萨克斯风在夜空飘扬,哀伤、寂寞,或者甜蜜、喜悦,浪漫极致的高音萨克斯风中我们都开始一段翱翔在深情旋律上的美好晴光……没有教学的繁杂,没有工作的疲惫,音乐似水,我裸浴其中。喧嚣的城镇也开始安静,与我一起寂寞又默契地感受一种浓郁芬芳的升华与密集的沉淀。
还有,我要带着我的亲人们一起吃饭唠家常,陪我的孩子一起蹲在地上看蚂蚁是怎样穿过一座小沙堆,看月光是怎样泛在青草尖上,看童年的风筝究竟可以飞上哪朵云彩……我要陪大家看一部也许我会觉得很无聊的电视,跟他们说些课堂上我永远说不上的笑话。一次远行,几声高唱,山水与我一起惬意。或者周末了,我也许整天上网,发几个帖,转几个段子,累了,洗洗脸,睡觉,如此等等。
我还可以想出很多的乐子,供我慢慢触摸,细细舔舐。
只是,别让我只扑在“教育”这个词上。谁都不可以夺走我自己的时间。
别总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要求我,因为除了教师这个角色,我们还有其他的身份。
别要求我奉献得太多,尤其在我感到身体疲惫的时候。
我可以是蜡烛,但请允许我源源不断地为自己添油剪花,我不愿意永远用微弱的光烛照我暗淡的前程。也请你别用孺子牛的缰绳捆缚我生命的步履,作为教师,我必须要有一亩幸福的田地耕耘,但,我不做赢弱却耕耘不辍的病牛,这样的姿态,我不接受。
我一直希望,站在语文讲台前的我健健康康,我声音洪亮,我精神焕发,我阳光生动,我耳聪目明。我不愿意用干涩的喉咙破坏美文的诵读,我不愿意以衰败的身躯支撑教学的天空,沧桑的表情无法激活学生的思维,灰暗的眼睛又怎能点燃他们心田热爱的明灯?一天的疲惫,我撑住了,那是我的敬业。长期积劳成疾下的如此敬业,又能有多少真实和效率可以送给我亲爱的孩子们?爱,需要激情,更需要理智,懂事的学生需要的是身心健康的老师,而不是拖着病体一味用感动来垫高的授课者。
病了,我就会休息。累了,我应该放松。看,休憩之后的奔流更有力量。听,调整之后的步伐更为坚实。懂得进退的人生才是真有意义的人生,深谙动静之理的工作才最能体现高效率。
负责,就是对教学效率的 教育的基石是真实,感动的背后其实是摧残,摧残自己,摧残学生,摧残课堂,摧残教育。病牛犁不出好田,荒土种不出茂盛。我干瘪的眼神,是上不好感动的语文课的。所以,累了,就歇歇吧,放手几节课,孩子依然在路上鲜亮地成长。
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并不要求我做太阳底下最无谓的牺牲。奉献教育,不是短暂的生命消耗,而是该有持久的动力支撑。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