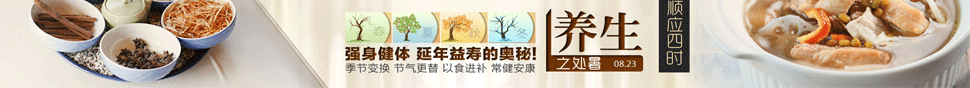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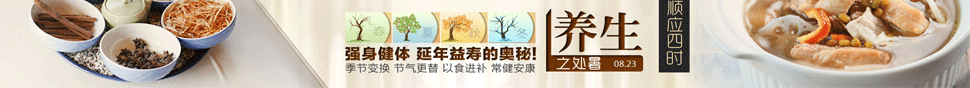
编者按
岳永逸从年开始研究燕京大学的社会学、民俗学论文,在大量的阅读中,他发现今天的中国社会学曾有着丰沛的民俗学底色,而中国民俗学的前辈们曾经努力实现学科的社会科学化。中国的社会学和民俗学原本曾是两位一体。当年开疆拓土的前辈,如今在学界多已默默无闻,他们的研究领域和成果在当下的学术界也常常处于“缺席”状态。如岳永逸所说,他要纪念的便是这段“因忘而缺的历史”。
为了忘“缺”的记忆:社会学的民俗学
文岳永逸(《读书》年6期)
#1
民俗学,又有“日常学”之称。作为一门学科,尽管其起源与民族主义、浪漫主义等与现代民族国家相连的思潮有关,但因为它同样是对抗启蒙主义(theEnlightenment)的产物,所以天然具有反抗性、在野性(岛村恭则:《民俗学是一门怎么样的学问》,《日常と文化》二〇一九年第七卷)。不难理解,作为#2
随着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美国社会学家、民俗学家孙末楠(WilliamG.Sumner)以民俗学说——Folkways——为核心的社会学说的引入,以燕京大学(燕大)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为阵地和该系师生集团性的努力,中国民俗学在此前先后以周作人为中心偏重文学的民俗学和以顾颉刚为中心偏重史学的民俗学主脉之外,演进形成了“社会学的民俗学”抑或说“社会科学化的民俗学”这一支派。孙末楠(转引自《社会学刊》年第一卷第一期)在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民俗学的社会科学化虽然有着孙末楠和杨堃译介的汪继乃波(ArnoldVanGennep)等人学说的外力,有着社会学、人类学的主动加盟,但同样是其内发性发展的必然。在此学术自觉的历程中,顾颉刚、江绍原、杨成志、钟敬文、娄子匡等人扮演了关键角色。更加重要的杨堃、黄石(字华节)、吴文藻、李安宅、赵承信、黄迪(字兆临)以及燕大诸多优质的毕业论文,则基本在既有的中国民俗学学术史的视野之外。更不用提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辅仁大学FolkloreStudies(《民俗学志》)上刊发的司礼义(PaulSerruys)、贺登崧(WillemGrootaers)等传教士在北中国完全基于田野的精彩民俗学研究。反向观之,对于中国社会学而言,尤其是后来被学术史家窄化为燕京学派——社区——功能学派的燕大社会学,有着深藏不露的民俗学(Folkways+Folklore)基底。在燕大社会学的本土化演进中,对同一研究对象经历了别有意味地从“风俗”(偏于史学)到“民俗”(偏于文学),继而快速到“礼俗”(偏于社会学)的交错更替。在相当意义上,当今中国社会学在本土化问题上的焦灼,也是多少忽略了其发轫之初立足风俗、乡土和国计民生的脚踏实地。而且,当这种焦灼并非基于小民百姓、乡土日常与生老病死等生活态时,就会不自觉地滑向方法主义、数据、建言献策的泥潭和术语堆砌的七宝楼台,并少了一门学科应有的独立思考与批判精神。邢炳南毕业论文封面要更为全面地认知中国民俗学史和社会学史,就不得不直面它们共有的“盲区”与“黑洞”。那就是,卢沟桥事变后,在民俗学与社会学合流与合力下,由赵承信设计、主导的对燕大“社会学实验室”平郊村(前八家村)长达近十年(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一,一九四五至一九五〇)的研究。仅燕大学士毕业论文而言,完全以该村为研究对象的多达十九篇。其主题涉及方言俚语、稗话传说、灵验故事、生产生活、政治经济、家族性别、组织分层、教育实践、宗教信仰、器具房舍、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庙庆市集……已经出版并深受好评的李慰祖的《四大门》仅是其中一篇。事实上,平郊村原本就隶属燕大清河试验区(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也即,燕大师生对平郊村的持续观察、调研长达二十年。在相当意义上,平郊村见证了燕大社会学以及中国社会学与民俗学在二十世纪前半叶的演进。平郊村的“犁”和“磨”(邢炳南,《平郊村之农具》)对于此前人文色彩厚重的中国民俗学而言,在平郊村的民俗学研究中,局内观察法、访谈法、个人生命(活)史、社区论、功能论、社会均衡论等方法和理论的加盟,夯实了中国民俗学的“社会学的民俗学”这一流派,实现了民俗学向社会科学的转向。对于燕大社会学而言,作为其重要的研究对象,从基于文献、区域的风俗研究到向村落社区的人生仪礼、生命史等礼俗研究的过渡,使引进来并尝试创新与在地化的社区—功能论有了充分的实践,生机盎然,硕果累累。毫无疑问,在中国社会(人类)学史中被施以浓墨重彩的燕京学派,是以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师生等为中流砥柱的。但是,许仕廉、杨开道等人主导的燕大清河试验区研究,吴文藻、费孝通先后主政的魁阁系列研究,及与魁阁工作站同期开启并有杨堃加盟,赵承信、黄迪主导的社会学实验室平郊村研究,这三大集群性研究才是与燕大社会学对等的燕京学派三大柱石。当然,这一切都与步济时(JohnS.Burgess)、甘博(SidneyD.Gamble)两位燕大社会学系创建者重视社会服务、社会工作而身体力行的社会调查紧密相关,尽管二人的学科建设与社会调查有着服务传教的色彩。林耀华,图片来自年《燕大年刊》地处国统区昆明呈贡的魁阁工作站着力点在土地制度、工业化、经济等大议题,更偏重社会、国家,有着与国外其他机构、学者的频繁互动,成果有着不同范围的发表、出版,有着先天的“政治”正确和话语优势。因此,对魁阁研究的再诠释、再提升,红红火火,绵长不绝。因着力乡村建设与试验,借当下新农村建设、乡村城镇化和脱贫攻坚等时政、要政,对燕大清河试验区之再研究同样顺理成章,有板有眼。与此不同,无论对于中国民俗学还是社会学,当年两者合力 虞权毕业论文封面对于个体、学科甚或人类而言,记忆与遗忘这对生死冤家,谁也少不了谁,谁也左右不了谁。在《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中,尼采有言:“快乐、良心、对未来的信心、愉快的行为—所有这些,不管是对个人还是对民族而言,都有赖于一条将可见清晰的东西与模糊阴暗的东西区分开来的界线而存在。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时候该遗忘,什么时候该记忆,并本能地看到什么时候该历史地感觉,什么时候该非历史地感觉。……对于一个人、一个社会和一个文化体系的健康而言,非历史的感觉和历史的感觉都是同样必需的。”或者,对青史留名的大师,应该多些“非历史感”,避免过度诠释和消费带来的“学术啃老”;而对无名过客,应该多几分“历史感”,因为或许正是在他们那里,潜伏着更多的希望,能够让后学豁然开朗。《旧约·传道书》有言:“Thereisnothingnewunderthesun”。阿铎(AntoninArtaud)曾冷酷地一语道破很多人不敢说或不能说的真相:“因为生命会不时地发生突变,然而这永远写不进历史,我也绝没有写过说要固定和永存那些删节、那些分裂、那些断裂、那些骤然失落的记忆,而那些无底的东西,它……”*文中图片未注明来源者均由作者提供
?文章版权由《读书》杂志所有
转载授权请联系后台
相关精彩文章
岳永逸:学术“同工”杨堃的批评天眼、日常生活与街头巷尾李培林:经济社会学思潮与罗桑瓦龙苏国勋:由社会学名著想到的——社会学的发展沿革费孝通:从反思到文化自觉和交流
本文编辑:佚名
转载请注明出地址 http://www.yizhijiana.com/yzjgj/18135.html

